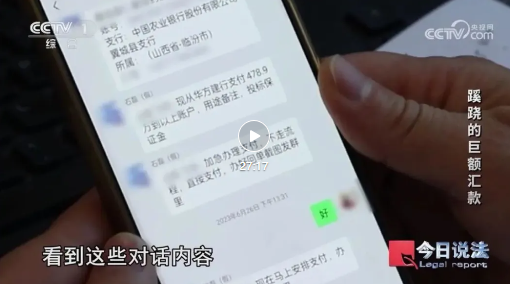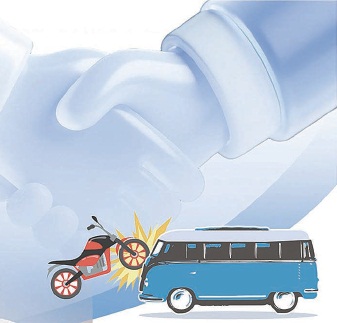

在检察官的见证下,李某(左)和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握手言和。

办案团队成员结合李某的通勤轨迹图,对案件进行复盘。
李某将目光停留在协议书中“11万元赔偿款”那行字上,滑动手指逐字确认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近日,在贵州省兴义市takse6的接待室里,当事人李某与贵州某信息技术公司(下称“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签署了和解协议,一场历时近4年、引发7次诉讼的工伤赔偿“马拉松”终于抵达终点。
这场漫长的维权“拉锯战”,源于一次通勤路上再寻常不过的亲情搭载——李某在骑车上班时,顺路捎上了自己的母亲。
通勤被撞
公司以“处理私事”为由不认工伤
2021年11月24日,时任技术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的李某,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上班,后座上坐着他的母亲。因每日母子俩通勤时可以同行一段路程,李某总会顺带捎上母亲。
李某骑行至一交叉路口时,一辆失控的小型客车突然撞了过来……这起交通事故导致李某和母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李某左腿多处骨折,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事故发生后,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型客车司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李某无责任。后经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李某构成九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小型客车司机赔偿了李某医疗费等费用。李某认为,自己是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属于工伤,公司理应为他申请工伤认定,使他获得工伤待遇。然而,当李某出院后申请工伤认定时,公司人事部门的一纸答复却将他打入冰窟:“经核查,李某在发生事故时,车上搭载有家人,属于处理私人事务,公司不予申报工伤。”
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提出,公司《考勤管理规范》规定14时前必须到岗,而李某遭遇交通事故时为当天14时36分,而且,当时李某的摩托车上搭载着家人,他显然是先处理私事再去上班,这属于私人行程,与工作职责无关。
经过讨论,技术公司根据《考勤管理规范》等公司管理规定,认为李某的行为性质是处理私人事务,不符合“上班途中”的工伤认定要件,拒绝为其申请工伤认定。
七次诉讼
“公私”之争激烈碰撞
2022年12月12日,李某带着《试用期合同》、详细的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等证据来到黔西南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州劳动仲裁委”),要求确认与技术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州劳动仲裁委审查后,支持了李某的诉求。
技术公司不服裁决,随即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作出与仲裁裁决一致的判决:李某与技术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23年7月19日,李某向黔西南州人社局正式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人社局认为李某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情形,认定李某所受伤害为工伤。技术公司对此结果不服,以人社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2024年2月21日,法院经审理认为,人社局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技术公司的诉讼请求。技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技术公司申请再审后,于同年11月5日被贵州省高级法院裁定驳回。
2024年12月4日,州劳动仲裁委裁决,技术公司须就超出工伤保险基金赔付范围部分,支付李某各项工伤待遇共计11万余元。然而,李某认为赔偿金额偏低,技术公司则坚持其“不该赔”的立场。双方均不服裁决,提起民事诉讼,将“战场”延伸至赔偿金额的确定方面。
今年3月27日,一审法院判决技术公司支付李某各项工伤待遇合计18万余元。4月,技术公司在提起上诉的同时,向黔西南州takse6提交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申请,请求检察机关对三级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依法进行监督。
调查核实
搭载母亲并未中断上班途中状态
由于技术公司和李某都在兴义市,黔西南州takse6受理案件后,立即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抽调兴义市takse6办案骨干组建检察官办案团队,共同办理此案。
主办检察官张静审查案卷材料后注意到,虽然在7次诉讼中,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多达数十份,但核心争议都聚焦在两个问题上:“上班途中”的状态是否因搭载母亲而中断?事故发生时间(14时36分)是否属于“合理时间”?
针对李某坚称“母亲下车点就在我上班路线途中,从未绕行”的说法,办案团队通过城市交通监控系统,调取到李某自2021年7月至11月间的摩托车行驶数据,并借助技术手段,将李某半年内的通勤路线绘制成轨迹图,对李某的日常上班路线用红线标注,对其母亲下车的点位用蓝点标记。结果显示:所有蓝点均在红线上,证明李某搭载母亲为顺路搭载,没有改变其上班的路线和所需时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第六条,“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因此,应当认定李某发生事故时确系在上班途中。
与此同时,办案团队调阅了技术公司内部的《考勤管理规范》。该规范载明,技术公司实际执行的考勤制度是“早晚各打一次卡”,对于下午的具体到岗时间并无强制性的打卡要求和精确到分的约束。
此外,办案团队还走访了技术公司的相关人员,了解到李某作为该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外勤,实际到岗时间并不固定,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也提到李某的工作特殊性导致上班时间、地点不固定,并非要在确定时间和地点才算在“合理时间”的“上班途中”。检察官认为,《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第六条对“合理时间”的界定不能被机械、僵化地理解为制度所规定的上班时间,而应结合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和特点、日常通勤所需时间、交通状况、长期形成的通勤习惯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应当认定,李某在事发当日属于在“合理时间”前往公司途中。
综合以上证据,检察机关认为,李某未改变既定上班路线并在所需时间的合理范围内顺路搭载母亲的行为,完全符合人之常情,不应被视为中断上班途中状态转而处理私人事务。并且《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有关“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并未对交通工具上是否可载他人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因此,人社局对李某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的判决、裁定亦无不当。
促成和解
司法温度融化多年坚冰
法律层面的争论虽然有了结果,但长达4年的诉讼对抗已在李某与技术公司之间累积了深深的矛盾。检察官深知,如果只是简单地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虽然符合法律规定,却把矛盾重新推给了双方,李某期盼已久的赔偿款依旧遥遥无期,而技术公司因李某申请财产保全被冻结的账户也无法获得解冻,经营将深陷停滞泥潭,案件最终可能走向两败俱伤的结局。于是,从彻底解决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办案团队决定开展矛盾争议化解工作,努力引导李某和技术公司达成和解。
在工作初期,技术公司对工伤认定决定仍心存芥蒂,对检察官的释法说理颇为抵触。检察官耐心地与公司负责人沟通,结合证据讲清案件事实,并逐条解析《工伤保险条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特别强调了“合理路线”和“合理时间”的认定标准。检察官用扎实的证据和严谨的法律分析,使技术公司负责人的固有认知开始有所改变。经过近一个月的释法说理,技术公司管理层最终认可了李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旧的矛盾刚解决,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无奈地坦言:“公司想赔付,但这几年光打官司就花了20多万元律师费和诉讼费,法院判赔18万元,公司账上实在没有这么多钱了。如果公司被强制执行,恐怕只能申请破产了。”张某的这番话让坚持要求全额赔偿的李某怒上心头,和解工作陷入僵局。
面对这一情况,主办检察官张静决定转换思路。她先与李某进行沟通,说明公司账户被冻结后,已有一段时间发不出员工工资,若真走到破产清算的地步,赔偿金很可能要等数年,还告知李某技术公司欠着供应商货款,项目款也没有收回的困境。李某思索片刻后,不甘心地说:“我不是非要逼死公司,就是想拿回自己应得的赔偿金。我也知道,如果公司真的破产了,我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如果分期付款,既能保障你优先受偿,也有助于公司恢复经营能力。”张静结合破产法的相关条文解释道,同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和解方案:将赔偿金降至11万元,但要求公司在三个月内付清,并附上法定代表人连带担保的条款。“这样既能避免执行风险,也能确保你早日拿到钱做康复治疗。”
与此同时,办案团队成员“背靠背”地做技术公司的工作。在得知李某愿意让步后,张某松了一口气,但表示时间太紧,很难凑到足够的钱。之后,又经过多轮磋商,双方终于就赔偿问题达成初步共识。
日前,在检察官的见证下,双方握手言和并签订和解协议:李某同意将工伤赔偿金降至11万元,放宽给付期限至今年9月底,同时向法院撤回对该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技术公司不再就工伤认定提出异议。双方签署完和解协议后,技术公司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撤回监督申请的书面材料。和解协议签署当天,二审法院以该协议为基础,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至此,这场历时近4年、历经7次诉讼的工伤认定与赔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